海外考古大家访谈|马克·波拉德:以考古意识为本位的科技考古学家
- 金融分析
- 2025-04-19 11:19:37
- 8
马克·波拉德(Mark Pollard),国际著名科技考古专家,国际科技考古权威期刊《考古测量学》(Archaeometry)主编,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Art)主任,牛津大学东亚考古、艺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波拉德教授1953年出生在新西兰,父母都是英国人,幼年随父母回到英国定居。大学时代在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学习物理学,1980年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84年到199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University of Cardiff)考古系与化学系任教;1990年,担任教授并被聘为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科技考古系主任;1999年,担任该校副校长。2004年至今,波拉德教授回到牛津大学并担任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主任。波拉德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古代物质文化(包括玻璃、陶瓷、石器、金属器等)、火山灰年代学、骨化学及稳定同位素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超过220篇,学术专著数部,如《科技考古概论》(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中的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in Archaeology)、《化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Archaeological Chemistry)等。

马克·波拉德教授
据我所知,您出生在新西兰,在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回到英国,而后在英国长大。在不同国家成长的经历,是否使您天然地对于不同文化感兴趣?另外,这种成长背景对您理解和研究不同文化是否有帮助?
马克·波拉德:是的,我的确是在新西兰出生的。我父母都是英国人,他们当时在新西兰工作。不过我不到1岁的时候就随他们回到了英国,所以严格来讲,我不算是成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因为我对1岁之前在新西兰的经历完全没有印象,虽然我在成年之后多次回到过那里。但是我想说的是,幼时在新西兰生活的经历虽然没有给我留下记忆,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却能够意识到我与其他人的不同,我不会天然地把自己定位成英国文化的承袭者而排斥其他文化,或者天然地把其他文化当作是外来的体系而不愿接近。这种没有记忆的幼年的经历对我还是有影响的,至少让我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并非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我想这对我日后选择考古研究作为我的终生职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您在大学时一直学习物理学,并且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但博士毕业后却一直从事考古学研究,是什么原因让您从物理学专业转而进入考古学领域?您的科学背景对您从事考古学研究有帮助吗?
马克·波拉德:我是学物理出身的,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约克大学物理系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约克大教堂上的中世纪玻璃花窗,当时主要是研究它的成分和成色机理以及几百年来它的物理性质的变化。这个题目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科技考古题目(Archaeological Science),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考古学的研究和一些考古学家。我在约克大学读博士期间,约克大教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在现在大教堂的下面,还叠压着维京人占领时期的教堂。在当时,这里是整个北方地区维京人的中心。在中世纪之前,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当一个族群占领了一个本来由其他族群控制的城市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把原先的中心建筑保留,而是将其摧毁,而后在原址上再建新建筑,以表示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我家就在约克郡,因此我每年暑假都作为志愿者参加约克大教堂的发掘。在这期间,我对考古发掘的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当时,我接触了很多考古学家,他们都是非常有趣的人,爱好广泛,而不像物理学家,多多少少有点刻板。这使得我在跟着这些考古学家工作的时候非常享受,是很愉快的过程。后来我越来越对考古学着迷。你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很好,物理专业的博士生非常容易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并不想一辈子都跟刻板的物理学家打交道,我无意冒犯他们,我只是感觉那种生活可能不适合我。所以后来,当我有机会可以从事考古学研究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转换了自己的专业。我的物理学背景对日后的考古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科学方面的训练让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采用多种方法去研究。并且,我会比较容易地与考古学家以及从事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沟通。这种沟通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我经常会听到您提及您年轻时的旅行。现在因为学术原因,您也经常要去世界不同角落出差。在旅途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旅行的经历是否让您对其他文化更加感兴趣?
马克·波拉德:我的确非常喜欢旅行。可能是我出生在国外的原因,我从小就对英国以外的国家和文化感兴趣。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旅途经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去南斯拉夫旅行。那时还是冷战时期,西方人进入东欧非常困难。我先去了希腊,然后从希腊乘火车进入南斯拉夫境内。当火车行驶到南斯拉夫边境时,有警察登上列车对所有乘客进行严格的检查。第一波来的警察拿走了我的护照说要进行仔细核查,然后第二波警察又来检查护照,我告诉他们我的护照刚刚被他们的同事拿走,但是这个理由不被接受。他们暗示我要给点钱来摆平此事,但我当时还是学生,身上没什么钱,而且我也不认为应该给钱了事,双方僵持不下,最终我被强行带下火车,在南斯拉夫的看守所里度过了24小时。现在回想起来,这只是旅行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很有意思,因为旅行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经历。这次在看守所里的经历不但没有减少我对旅行的兴趣,反而令我对不同国度、不同制度、不同社会文化更加着迷,让我开始尝试去了解和理解与我生活的环境不同的其他社会。我想这可能也是我日后转到考古学领域的一个思想准备。
您是在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完成的博士后研究。以物理学博士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考古学实验室做博士后,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20年之后,当您再次回到这个实验室并成为实验室主任的时候,您对这个实验室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马克·波拉德:能够来到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简称RLAHA)做博士后是非常幸运的事。这个实验室成立于1955年,虽然比大英博物馆的实验室要晚一些,但大英博物馆的实验室主要为馆藏样品做保护,所以RLAHA是全世界最早的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实验室,在考古学界享有盛誉。我从约克大学毕业后,遇到了RLAHA的创建者、当时的实验室主任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教授。他是一个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绅士,同时非常平易近人。我当时想来RLAHA工作。他问我对考古学了解多少,我如实回答非常有限,但是很感兴趣。一个星期后,我就来到了RLAHA,跟着爱德华·霍尔教授一边学习一边从事物质文化的研究。他总是尽可能地给年轻人提供机会。1982年他资助我与中国艺术史专家杰西卡·罗森教授(Jessica Rawson)、中国陶瓷专家奈吉尔·伍德教授(Nigel Wood),一起来到中国参加古陶瓷学术研讨会,并参观考察了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自那以后我又多次来到中国,可以说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考古学家,但是对中国陶瓷的研究是我在RLAHA作博士后期间的主要研究内容,也为我日后从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在RLAHA的研究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非常多有才华的同事和深厚的研究基础,很多科技考古的新技术和新方法都是在这里诞生的,从这里也走出了很多大家,比如泰特教授(Michael Tite)、亨德尔森教授(Julia Henderson),马丁·琼斯教授(Martin Jones),海吉斯教授(Robert Hedges),马松教授(R.B Mason)等等。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开始考古学研究,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和研究思路,对我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离开RLAHA之后,去了卡迪夫大学和布拉德福德大学继续从事考古学研究。2004年,在我离开RLAHA20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并担任了实验室成立以来的第三任实验室主任。20年中,我虽然不在这里工作,但与RLAHA一直都有密切的联系,并开展了很多合作研究。它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学术传统,为实验室的学生和学者提供良好的研究平台,并为全世界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学者提供交流和讨论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它还为科技考古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RLAHA曾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了碳十四测年的技术并提供了设备。我认为RLAHA一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之一。要说这20年时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它的研究方向更加多样化,从传统的陶瓷、玻璃、金属等无机材料,扩展到动植物、环境、残留物、火山灰等方向。关注的地域也更加广阔,从欧洲为主扩展到非洲、中东、中亚、南亚、远东以及美洲和大洋洲等有人类活动的所有大陆。研究者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我们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了,除了欧洲和英语国家的学生,还有来自印度、墨西哥、韩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留学生。我希望有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学生和学者能够来到RLAHA从事考古学的研究。我相信这无论对实验室、对研究者还是对科技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除了物质文化,您对测年技术也有研究。您如何评价测年技术给考古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据我所知,在某些领域,比如对地中海地区古典时期的研究中,很多考古学家认为陶器的类型学分类和断代要比现代的测年技术更准确。您如何看待部分考古学家对现代测年技术精确性的质疑?
马克·波拉德:测年技术是科技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测年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碳十四测年技术的使用,给考古学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绝对的时间标尺,使得原先对不同地域的、相对孤立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可以进行比较的时间依据,为考古学从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碳十四等测年技术并不是唯一的考古学判断年代的工具。正如你所说,基于类型学的陶瓷分类和断代也是重要的判定年代的手段,特别是对特定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类型学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比如在地中海地区古典时期的研究中,陶器器型的年代判断可以精确到25年的范围,这是目前碳十四等科技测年手段尚不能达到的精度。另一方面,科技测年技术还有一些明显的劣势,比如成本很高,得到结果的周期也比较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陶器类型学断代的技术是不会被取代的。各种测年断代的技术和手段都有各自的优势,应该综合考虑,发挥不同技术的优势,对不同的研究时期和对象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方法。总的来说,科技测年的技术与史前考古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您能否谈谈科技考古的历史?它与考古学是什么样的关系?您如何评价20世纪60年代的新考古学运动?
马克·波拉德:科技考古实际上一直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就有零星的对古代遗物的化学分析工作发表了。早期的考古学借鉴了很多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基于科学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不过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 Science)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仪器分析手段的发展和完善而产生的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方向,它通过多学科的分析手段给研究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到更多之前可能被忽略的事实。成分分析使我们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从表面深入到了内部,DNA技术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的亲缘关系,同位素分析帮助我们了解先民食谱,而测年技术帮助我们建立时间标尺。通过对不同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我们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就更加全面而深入了。科技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在研究目的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技术手段上更丰富。因此,我认为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是考古学家,而传统的考古学家也应该对科技考古中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使科技考古学更好地融入考古学的研究中去。20世纪60年代的新考古学运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于关注技术手段和数据信息而忽视考古学背景。当时很多研究工作利用统计学理论建立模型来处理大量的测试数据,然后根据模型模拟的结果来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考古学背景,只注重数据本身,这其实等于简化了考古学研究的过程,而这种简化丢失了很多考古学信息,使得原本注重实物、实地和实证的考古学研究变成了实验室里的研究,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常常与一些考古学的常识相悖,被考古学家嗤之以鼻。这种脱离考古学背景的研究使科技考古的发展偏离了方向,所以新考古学运动没能持续下去。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新考古学运动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引入了更多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到考古学的领域中来,也吸引了一大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关注和思考考古学上的一些问题,对科技考古学的提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科技考古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客观的说,没有新考古学运动,也就没有科技考古学今日的发展。
在您的书中也曾提到过:“尽管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承认科学测年技术和其他的科学技术手段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了很多隐藏的信息,但是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常常缺乏某个具体的考古学问题作导向。”这是科技考古学目前仍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吗?
马克·波拉德:应该说在经历了对新考古学运动中过分强调数据解读的反思之后,大多数的科技考古研究工作都能结合考古学的背景和问题。不过也必须承认,缺乏具体考古学问题作导向的研究工作仍然存在。考古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包罗万象。在研究的过程中,田野材料的分析、背景文化的讨论、实物的测试以及文献的记载都是研究的材料。如果只注重某一方面而偏废其他,就难免存在缺陷。这不仅仅是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中仍然需要注意的,在考古学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考古学的研究一定要注重与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同行多交流、多合作,这样才能做出真正有水平的考古学研究工作。
您的学术经历相当丰富,不仅在三四所不同的大学任过教,研究的地域更是涵盖了亚、非、欧、美几大洲。您认为对您帮助或者启发最大的学术经历是什么?
马克·波拉德:我是专注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考古学者,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往往是跨地域的,所以我有机会从事各个大洲的物质文化研究。从我的经历来看,我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起步和顶峰阶段都是在牛津大学。我认为牛津大学独特的学院制体系及学术环境给我的启发和帮助非常大。这里我需要对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体系做一点解释,它其实是保留了大学最初开始形成时的体系,在12到13世纪时,王室、贵族和一些教会组织资助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开设学院,传播知识。所以不同的学院并不是以学科来划分的,当时还没有形成现代的学科概念。当时的学术主要是研究神学,而学院更像是以某几位学者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在现代学科建立起来以后,以系为单位的按照学科来划分的大学体系逐渐形成了,但是牛津大学仍然保留了学院系统。现在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由各个系来承担,而本科生的教学仍以学院为主。有人形象地把学院比喻成家庭,每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来自各个不同的系或专业,但是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的学院里,学院有宿舍、餐厅、图书馆、活动室,还给学生提供学业上的辅导。这种学院制系统给不同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充分的交流机会,因为你在学院的餐厅、图书馆、活动室遇到的同事其实来自各个专业。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受益于在牛津大学工作时的这种跨专业学者间的对话和讨论的。
据我所知,您对颜料,特别是蓝彩的研究很感兴趣。包括我自己在内,您有若干博士研究生在从事蓝彩的研究工作。能不能就蓝彩研究的意义和现状做一点介绍?
马克·波拉德:我这几年做了一些关于蓝彩的工作,而关注它的时间则更久远。实际上100年前就有学者对蓝彩进行了研究,发现埃及蓝(Egyptian Blue)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颜料并通过测试得到了它的组成成分。学者们对蓝彩关注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蓝彩出现得非常早而且使用很普遍,早在5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蓝彩陶器和玻璃器。除了天然的蓝彩矿物,埃及人甚至发明了人工合成蓝彩的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埃及蓝。在埃及之后的地中海古文明中,比如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Minoan Culture)和迈锡尼文明(Mycenaean Culture)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蓝彩装饰的壁画。这种对蓝彩的喜爱和使用延续到了其后的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甚至影响了伊斯兰文明。除了地中海地区外,我们发现在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中,蓝彩也有很特殊的地位。在玛雅人的墓葬中,只有非常高等级的墓葬才使用蓝彩做装饰。而且玛雅人也使用人工合成的蓝彩颜料,叫作玛雅蓝(Maya Blue)。与无机成分的埃及蓝不同,玛雅蓝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有机颜料,我的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博士生正在从事它的制备过程的研究。在远东的古代文明中,情况似乎与地中海地区及中美洲有所不同,蓝彩装饰的物质并不普遍,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晚。伴随着佛教石窟寺的兴建和青花瓷的出现,蓝彩才开始大量使用。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寺中使用的蓝彩,主要是由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加工而成的;而青花瓷所使用的蓝彩的产地还不是很明晰,特别是早期青花瓷的蓝彩产地,学术界的争议比较大。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的工作,能够使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区域的考古问题,它还涉及不同地域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传播,还有人类不同文明的差异。这是一个由物质载体而延伸到人类古代文明交流和比较研究的课题,因而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您与中国有相当深厚的渊源。您刚刚开始进入考古学领域时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后来您又多次来过中国,涉及陶瓷、玻璃、青铜等方向的研究。如果未来您有机会与中国的考古学家进行更深入的合作研究,您希望就哪个或哪些方向开展合作?
马克·波拉德:是的。正如你所说,我与中国非常有缘。我开始从事考古专业的研究工作后,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中国,当时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瓷器原料来源的工作。离开牛津大学后,我主要从事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包括伊斯兰地区的物质文化研究,但是我对有关中国的研究课题一直非常关注。去年牛津大学考古学院专门成立了东亚考古研究中心,目的也是为了能给关注东亚考古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个人也非常期待与中国考古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古代瓷器生产与当地环境的相互影响,及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传播这一类的课题。陶瓷专家伍德教授在多次考察了越窑、龙泉窑等窑址之后,对它们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大为惊叹,仅上林湖一地,就发现了几十座龙窑的窑址。这么大的生产规模,对原料和燃料的需求量也一定很惊人,而调制釉水的草木灰和烧造瓷器的木炭应该都来自当地植被,瓷器的生产对当地植被和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伍德教授甚至认为植被的破坏可能是越窑生产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能通过环境考古的方法,对这一课题做深入的研究。丝绸之路考古是100多年来全世界考古学家始终关注的课题,刚才提到的蓝彩物质的传播也是丝绸之路考古的一个方面。这条通路连接欧亚、沟通东西,通过这条通路传播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技术、文化、宗教、思想等等,我们对它的研究和了解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与中国考古学者合作,在这一领域做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2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下一篇:网络社群的早期历史及其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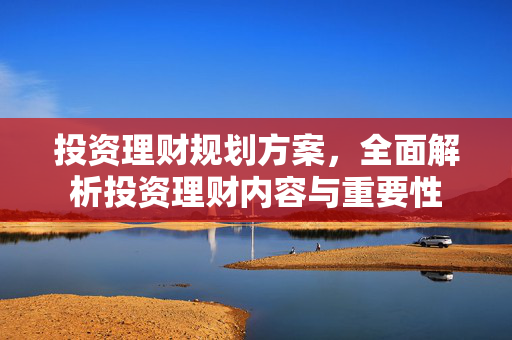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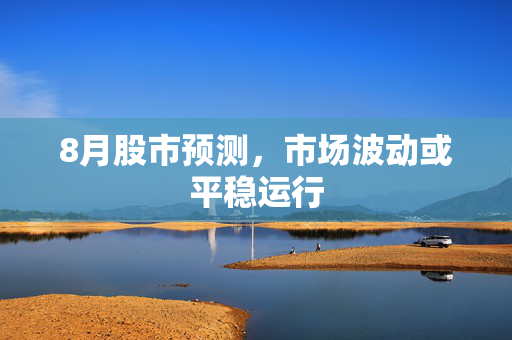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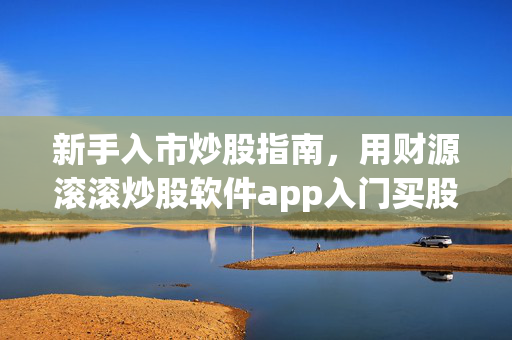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