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金茨堡:女巫与萨满——我的学术之路
- 科创板分析
- 2025-04-18 11:02:04
- 10
我的学术之路颇为漫长崎岖:它始于意大利东北部,我对巫术的研究便在那里起步,而后则一直延伸到了中亚的大草原。本文是对这条路径的一个总结回顾。
伟大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曾说过,“方法就是我们走过后留下的道路(la méthode, c'est la voie après qu'on l'a parcourue)。”“方法(metodo)”这个词,实际上源自希腊文,尽管葛兰言所给出的这个词源解释——meta-hodos,走过后留下的道路——或许要更加形象。但是,葛兰言的这句谐谑之言,却有着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以引发激烈争论的内核: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关于方法的长篇大论,都只有在对某项具体研究进行反思时才有价值,而不是在研究进行的当下(迄今为止,这都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形)预先设下一系列的规矩。我希望,接下来我对自身研究来龙去脉的方法论回顾,无论本身如何无足轻重,都能有助于重申葛兰言的这一讽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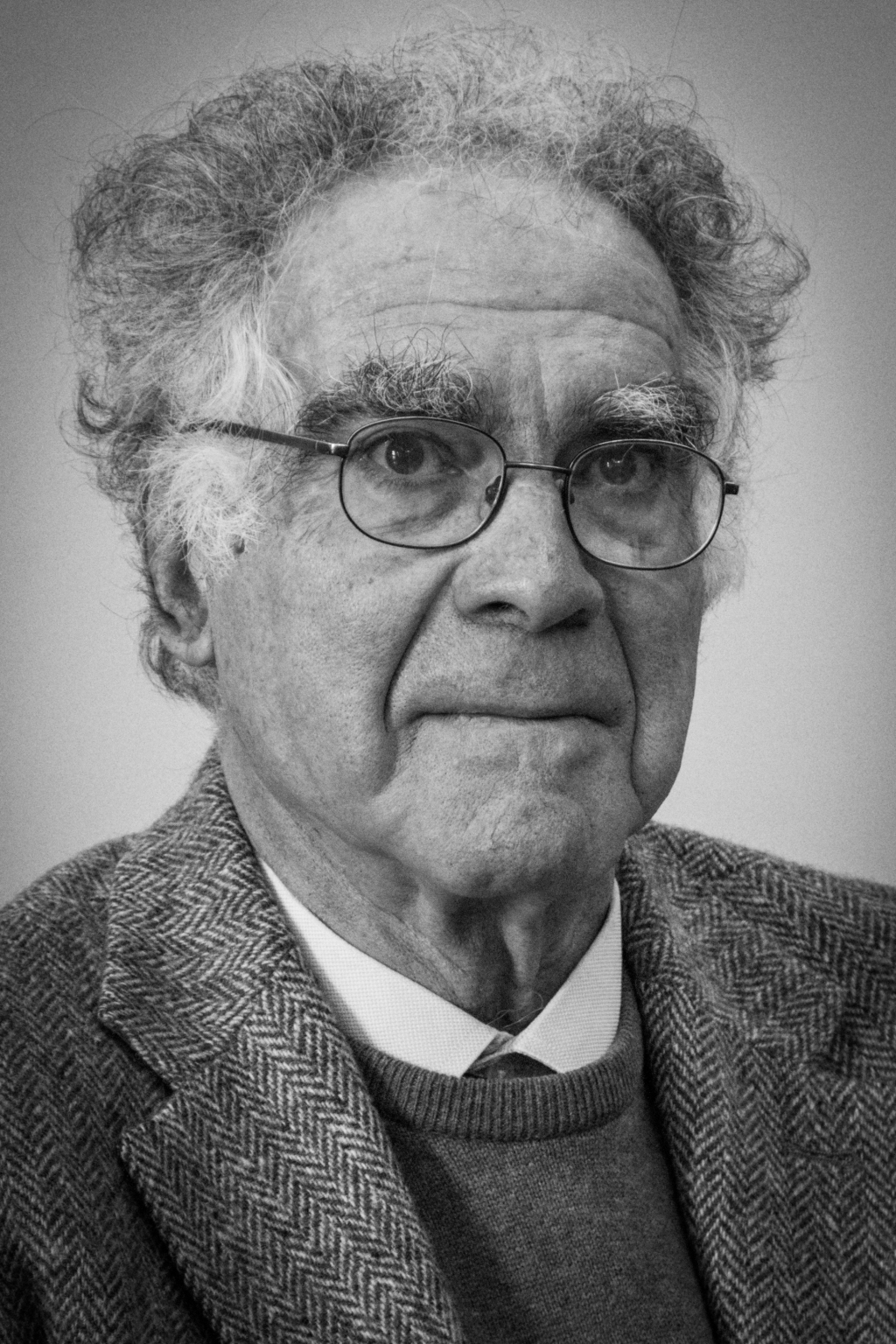
卡洛·金茨堡
对于一项如今已得出结论(尽管就其定义而言只是一个暂时结论)的研究,详述其步骤流程自然永远都会伴随着某种风险,那就是目的论的风险。回头看去,各种不确定性和错误全都消失了,或是转化成了笔直通向目的地的阶梯上的一级:这个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上下求索,终有所获。但在现实的研究中,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拿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这样拥有人类学背景的科学史家来说,他笔下所描述的实验室生活,就更令人困惑,也更错综复杂。
我将要在此描述的经验,很可能也是混乱无序的,即便它只牵涉到一个人——我自己——而不是一群人。一切缘起于50年代末,一个研究题目(巫术)突然闪现于一个20岁的比萨大学学生眼前。直到那一刻之前,我都并不确定,是否想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但当这个主题浮现于脑海之中时,我已别无疑惑。这就是我的研究主题,一个我准备为其投入多年心血的研究主题(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会是多少年)。
我曾经问过自己许多次,这突如其来的激情,这回头看去具备了陷入爱河的全部特征——迅如电光石火,狂若神魂颠倒,不知所起但却一往而深(至少表面上如此)——的冲动,到底是出于哪些原因。我当时对巫术历史一无所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中查找“巫术”这个词条,以获取某些基本信息(这种做法我后来在研究其他题目时又重复了许多次)。或许,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那种“无知的欣悦(euforia dell’ignoranza)”——那种一无所知而又即将开始学习某些东西的感觉。我想,正是与这一时刻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强烈快感,令我没能成为一名专家,没能在某一确定的研究领域深耕细作。那种阶段性地涉足一些我完全一无所知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的冲动,不仅一直保留了下来,而且多年来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个大二学生选择了自己一无所知的研究题目,这种事可谓稀松平常。但或许不那么寻常的,是一种觉察,那便是在一个人的存在过程中,所有或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选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对于那个十分重要的目标,我们往往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我们在回望过去时,将这种不相称叫做命中注定。)但是,又是什么让我们做出了选择?如今想来,在我当时对这个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研究题目的激情背后,或许藏着一团乱麻般的儿时记忆与经验,而它们又和后来的激情与偏见缠绕在一起。
那些在我孩童之时讲给我听的童话故事,在我的选择中占到多大分量?我的母亲从前经常给我读童话故事,它们是西西里作家路易吉·卡普阿纳(Luigi Capuana)在19世纪末收集整理而成的,其中尽是各式各样的魔幻和恐怖故事:母龙的血盆大口中,塞满了“形似小儿的羔羊”之肉;貌似无辜、头戴羽饰巾帽的小家伙,翻过一页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狼人。我们一家人曾经在阿布鲁齐住了三年,一个名叫克罗切塔(Crocetta)的当地小姑娘给我和我弟弟讲过一些故事,它们与卡普阿纳收集的那些并没有太大差别(我是从母亲纳塔利娅·金茨堡的作品《阿布鲁齐的冬天》中得知这一点的)。在其中一则故事中,一个孩子被后母杀死,然后被当成食物喂给了他的父亲。便在那时,他的骨头开始唱歌:“哦,我那邪恶的妈,把我放到热汤里熬,而我那馋嘴的爸,把我当成了美味佳肴。”透过这些童话故事中隐含的邪恶,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开始对现实做出解读,而首当其冲的现实,便是成年人的神秘世界。
在《夜间史》(Storia notturna)一书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人兽同感(antropofagia)和兽化变身(metamorfosi animalesche)。对我来说,决定研究巫术,马上就意味着把注意力聚焦在女巫的供词之上,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童年时听到的童话故事十分相似。但当时仅为我模糊感知的、做出此种选择的动机,其上却嫁接了情绪和意识形态的其他原因。我生于一个政治上左倾的家庭。我的父亲莱昂内·金茨堡(Leone Ginzburg)生而为俄国人(他出生于敖德萨),后来随家人移居到了意大利。1934年时,因为拒绝向法西斯政权宣誓效忠,我父亲失去了都灵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的职位。当时他只有25岁。没过多久,他就因为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两年时间。当意大利于1940年与纳粹德国一道参战时,作为一名犹太人和反法西斯分子,他被囚禁于皮佐利(Pizzoli),这是阿布鲁齐地区的一个小镇,离拉奎拉(L'Aquila)不远。他在那里得以与妻儿会合。法西斯政权垮台时,我父亲前往罗马,重新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随即被捕并被认出身份,于1944年死于纳粹控制下的圣母监狱。佛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在他的著作《俄国民粹主义》(Il populismo russo)中,提到了我父亲的为文与为人。两人在流亡巴黎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小圈子中结识并成为密友,而这个圈子是俄国民粹派(narodniki)精神的“全新化身”。正如我们所知,在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经验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一种对农民社会所表现出的价值观的强烈道德同情与智识同情。在一本战后出版并马上被译成多种语言的书中,我发现了同样的态度,这本书便是《基督停留在埃博利》(Cristo si è fermato a Eboli)。此书作者——作家和画家卡洛·莱维(Carlo Levi)——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两人曾一道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团体“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à),一起被法西斯政权囚禁于卢卡尼亚的一个小镇。我相信,正是这些平行轨迹,让《基督停留在埃博利》在少年时阅读此书的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种认同感油然而生,即便莱维描述的那个乡下,要比我度过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更闭塞荒凉。但是,打动我的,不只是这本书设置的故事背景。莱维丝毫没有掩饰他与那些南部农民在思想和信仰上的差异之处,但他从未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连咒语(incantesimi)和符箓(formule magiche)也包括在内。从《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中,我想我学到了如何在智识上置身事外而在情感上身处其中,如何在满怀激情地追求理性的同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些态度不仅是可以和睦共存的,而且能够彼此滋养。从我母亲那里,我还学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而且其重要意义不仅关乎我的研究工作),那就是智力无关于社会和文化特权。
回头看去,我认为,童年时听到的那些童话故事以及从家庭环境中吸收的民粹主义思想,都给我留下了深远的烙印,而这从很早的时候,便将我的研究导向了对被迫害者的考察,而不是只着眼于迫害本身。这是一个在双重意义上不走寻常路的历史书写选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长久以来作为人类学家经典研究主题的巫术,依然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比如曾对此冷眼旁观、嘲讽有加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认为是一个边缘且怪异的研究题目。
即便想为分析巫术迫害的正当合法性辩护,最多也只能将其认定为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欧洲智识史上一个偏离正轨的小插曲。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巫术居然变成了历史书写的一个流行主题:但历史学家的兴趣即便从形式上表现得比以往更多样,却依然近乎一边倒地聚焦在迫害及其文化与社会机制上。被迫害者依然一直身处阴影之中。
我已经列出了一些将我推向这一方向的原因。但在此我必须再加上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这种研究的难度。几年中,一些最重大的障碍逐渐浮出水面。而在当时,我看到的最突出的障碍,乃是这些巫术实践虽然发生在相距甚远的不同时间地点,可从表面上看其形式却十分雷同(但对巫术的迫害并非如此)。我当时便想,有必要将巫术重新引入历史,把它那些看似没有时间性的特性放到历史之中考量。这种想要发起某种认知挑战的渴望,毫无疑问带着一丝少年心气:想要向其他人证明,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证明,在那道被康拉德(Conrad)称为阴影线的临界之上,一个人到底能有何种作为。
我还遗漏了一个因素,而这是几年后我才意识到的。当时,一个朋友向我指出,选择研究巫术,尤其是巫术迫害的受害者,对于一个知道迫害为何物的犹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简单明了的观察令我震惊。我怎么会忽略掉了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然而多年来,犹太人与女巫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我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认同感的可能性,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意识中。如今,我倾向于在这一切之中看到压抑效应(effetto della rimozione)。弗洛伊德教导我们,那些明确存在但却隐而未现的,正是一个人不想看到的那些东西。
我要为如此长篇大论地讲述个人境遇而道歉。我很想克服那种自我凝视的诱惑,那种藏在每个人心中的、视自己为某项体外试验(esperimento in vitro)之数据的诱惑。一位历史学家的生平——从他的家庭环境,到他所受的教育,再到他的亲朋好友——对于理解其作品而言并非无关轻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或者至少应当被泰然处之。但通常来说我们都不会越过这条线。而我想要做的,是在身份认同(identità)这个经常被我们说起的词上做些文章(即便“接近[contiguità]”这个词或许要合适):这种身份认同,既是生理上的,也是个人意义上的。我想要回头细察一下,在如今的这个我与当时的那个我之间,那些与身份认同有关的因素,是如何介入到了我的具体研究之中。我已经列出的那些因素,帮助我选择了一个从某一特定角度(被迫害者)出发的主题(巫术)。但这些因素——无论是那些最受压抑的(身为犹太人),还是那些最清楚知晓的(想要跨学科的冲动)——都并不必然包含一个特定的研究猜想。我开始进行研究所依据的那个猜想——也即巫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原始初级形式——在今天的我看来,不过是在试图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某种缺乏真正历史书写正统性的研究确有必要而已。简而言之,我想要跨学科的那种冲动,并不是不受限制的。
在我的研究猜想之后,是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几篇文章的阅读:有两篇收录于《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1959),还有一篇最重要的,是他1960年发表在意大利共产党党刊《社会》(Società)上的研究综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了下层阶级的历史》(Per la storia delle classi subalterne),显然是在呼应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使用的术语。对我和我那一代的许多其他意大利学者而言,阅读葛兰西的作品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霍布斯鲍姆文中呈现的葛兰西,是一个透过了英国社会人类学滤镜解读和诠释的葛兰西。但是,我在那些年里接触到的人类学著作却另有出处:首先便是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那些作品,三十年后,他成了《夜间史》这本书的主要对话者。
我开始阅读保存在摩德纳国家档案馆中的宗教法庭审判记录。在这些故纸堆中,我偶然发现了一起1519年的案子,其被告是一位名叫阿纳斯塔西娅·拉弗拉波纳(Anastasia la Frappona)的农妇,她被控企图以咒语谋杀一位将她和丈夫从其耕作的土地上逐出的女主人。“历史学家通常都会发现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这一事实让我颇感窘迫。”研究犹太教和基督教起源的美国历史学家莫顿·史密斯(Morton Smith)如是写道。我并不确定,在发现这个对我的研究猜想——巫术作为阶级斗争基本手段——出乎意料的印证之时,我是否也感到了一丝窘迫。但事实上,我的研究随即便转向了另一条道路。这种斗争和对峙依然处于中心位置,但却转移到了文化层面之上,而这可以借助对文本的细读来破译。一些小说语文学家,比如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莱奥·施皮策(Leo Spitzer)、詹弗兰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将我推向了这个方向。从他们身上,我尝试着学到了将“慢读”[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醒我们,这才是语文学]应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之上的艺术。
我说的所有这一切,都带着后见之明:我并不想将某种当时我并不具备的清楚了然投射到过去。1961年到1962年间,我在意大利各地游历,追寻着宗教法庭档案的线索痕迹。我经历了一些自疑和自责的时刻;我感觉自己是在浪费时间。我最开始的那个关于巫术作为阶级斗争基本形式的猜想,已经不再能够令我满意;但我也没办法代之以一个更让我满意的猜想。我最后到了威尼斯,那里的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着最丰富的宗教法庭审判记录:150多个卷宗里,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审讯和审判记录,其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半世纪(从16世纪中期一直到宗教审判被废止的18世纪末)。每个学者每天都能请求调阅有限数目的卷宗:我记得当时对我的限制是3卷。因为一开始时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些什么,我便随机提出调阅请求——比如卷宗8、15和37——然后把审判记录浏览一遍。那感觉,就像是在玩某个梵蒂冈主题的轮盘赌游戏。之所以强调这些琐碎的细节,是因为它们让我得以着重指出,我的发现——1591年时针对一个来自拉蒂萨纳(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镇)的牛倌的审讯——具有绝对的随机性。这位名叫梅尼基诺·德拉诺塔(Menichino della Nota)的牛倌供称,每年四次,他会在晚上灵魂出窍,与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出生时带有胎膜、人称本南丹蒂(benandanti,当时我对这个词一无所知,而且完全无法理解)的人一道,在一大片遍生玫瑰的草地——约萨法特之原(prato di Josaphat)——上与巫师作战。倘若本南丹蒂们获胜了,当年便会五谷丰登;假如巫师获胜了,饥荒就将来临。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读完这份文献(不超过三到四页)之后,我进入了一种狂躁状态,以至于不得不停止工作。我在档案馆前走来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心里想着,这可真是撞上了大运。我依然是这么想的,但今时今日,光是这种就事论事已经不再能够令我满足。这件案子,让我置身于一份完全出乎意料的文献之前:为什么我的反应会是如此的热情洋溢?就好像是我在突然之间,辨识出了这样一份直到前一刻还完全不为我所知的文献的重大意义。不止如此,与我迄今为止接触到的所有宗教法庭审判程序记录相比,它都迥然不同。而我想要反思的,恰恰便是这一点。
在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有幸参加过詹弗兰科·孔蒂尼主持的一个研讨班。孔蒂尼突然停下来,开始讲起一则趣事。有两位小说语文学家,他们都是法国人,但除此之外则大相径庭。第一位留着长须,对形态学、语法学和句法学上的不规则变化情有独钟;每当发现一个这样的不规则变化时,他便会拈须欣然,念念有词曰:“怪哉怪哉(C'est bizarre)。”第二位作为笛卡尔哲学的正统传人,则是一个不仅头脑灵光而且头顶光光的学者,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每一种语言学现象都纳入规则之中。每当做到这一点时,他便会搓着手说:“诚赏心乐事也(C'est satisfaisant pour l'esprit)。”我很乐于承认,孔蒂尼提到的这两位语文学家所体现出的那种异常与类似的反差,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差,而这种反差,在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时代的语法学家身上就已经存在。然而,我必须忏悔的一件事是,我倾向于认同那位留胡子的语文学家——那个热爱不规则变化的家伙——的冲动。然而,出于某种心理习性,我也会想要从理性上加以证明。此外,对规则的违背,本身就包含了对规则的认可(因为这是以规则为先决条件的);但反过来却未必如此。在研究某个社会运转状况的时候,有些人会从这个社会的一整套规则入手,或者始于根据统计数据虚构出来的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女性,那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停留于浅表。我认为,对一个异常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产生更丰硕的成果(但我对苦思冥想孤立的异常事件并不感兴趣)。
我便是这样研究起了这起巫术案件。我从一个异乎寻常的文献(对本南丹蒂梅尼基诺·德拉诺塔的审讯)出发,重新构建了一个异乎寻常而且处于边缘地带的现象(弗留利地区本南丹蒂的信仰),而这反过来又给了我一个密钥,让我得以据此破译遍布整个欧亚大陆的大范围巫师夜间集会实践(sabba stregonesco)的起源。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夜间史》,还是出版于20年前的《夜间的战斗》(I benandanti),都诞生于多年前在威尼斯国家档案馆中偶然发现的这三页纸。是什么让我对这样一份全然出乎意料的文献做出如此热情洋溢的反应?我曾如此自问。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了:原因,恰恰便是这份文献所具有的那些会让其他人视其为无足轻重、甚至索性弃之不顾的特征。今时今日,一个16世纪牛倌讲述的关于其出神体验的故事,一个充满童话色彩而且绝对异乎寻常的故事,很可能会被严肃的历史学家当成一份生动形象的证词,用来证明那些对教会权威制定的指令坚决避之不及的人是何等愚昧无知,而在三十年前,就更是如此。
与本南丹蒂梅尼基诺·德拉诺塔审讯记录的邂逅,完全有可能从未发生。然而,有时候我会想,这份文献就是在那儿等着我,而我的全部往昔经历,都在准备着这一次相遇。我坚信,在这个荒谬的想法之中,含有一个真相内核。正如柏拉图教导我们的,求知(conoscere)永远都是一种辨识(riconoscere)。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些已经成为我们经验财富一部分的东西,只有借助它们,我们才得以获取新知,将这些新的知识从不断掉落的那些无序、随机的海量信息中厘清辨明。
在这些始于15世纪初、止于17世纪中叶后、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欧洲巫术审判中,我们几乎一直都能看到某种单向交流的存在,这种交流是在强迫下进行的,辅之以心理诱导和肉体折磨。那些法官,无论是世俗法官还是教会法官,都知道自己应当从被告人口中得到何种答案,而且会用诱导式的提问或强制力量来促使后者招供。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自己寻找的答案:有时候,被指控的男犯女犯一直宣称自己无辜,或是熬刑不过而瘐死。当然,并不是被告人所供述的每一件事,都是法官施压所致:对那些求爱咒或索命咒的描述,显然来自一个不同的文化,一个专属于被告人的文化。但在巫师夜间集会——伴随着纵酒、宴乐、崇敬魔鬼等活动的夜间聚会——这件事上,那些被控行巫术的男男女女,似乎却在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同一个阴谋计划,而只有少许出入。这个阴谋计划,似乎是由鬼魔学家们精心设计出来的,而后被发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巫术审判强加到了这些被告的身上。
从对本南丹蒂的审判中浮现出来的一连串的景象,却是完全不同的。法官与被告之间沟通交流的全然阙如,构成了这些审判(尤其是年代最久远的那些)的主旋律。通常无需诱供,这些本南丹蒂就会说起他们在夜间以灵魂出窍形式进行的那些以祈求丰产为目的的战斗:他们会以茴香秆为武器,与手持高粱秆的女巫男巫作战。所有这些,对于宗教法庭审判官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就连“本南丹蒂”这个词,他们也一无所知。而在50多年的过程中,他们反复地询问这个词的含义。正是这种缺乏交流,让一个深藏地下的信仰层得以显露出来:这是一种以丰产为中心的出神崇拜(culto estatico),其受众为意大利东北部边境的弗留利地区以及威尼斯共和国下辖部分地区的农民,而它在16到17世纪时依然生机勃勃。
在最初的晕头转向之后,宗教法庭审判官们试图帮自己确定方位。因为这些为祈求丰产而在夜间战斗的故事令其联想起巫师夜间集会,他们便努力迫使(并未诉诸刑讯)本南丹蒂们承认自己是巫师。本南丹蒂面对这些施压,激烈地予以反抗,但接下来,一点一点地,他们屈服了。在他们时间跨度长达50年的供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巫术实践中巫师夜间集会的形象一点一点地渐渐出现。我们可以一步步地追踪这一缓慢的变形过程,而它让我产生猜测:一种类似现象——将巫师夜间集会的形象强加于某个居于其外部的信仰层之上——可能也曾发生于弗留利以外的地区。
但我试图在《夜间史》中证实的这种猜测,依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出神体验的事,而本南丹蒂们曾以栩栩如生的细节讲述过这些体验。与宗教法庭审判官不同,我没办法对本南丹蒂们讲述的故事施加影响。但我和宗教法庭审判官一样,试图对我遇到的这种异常现象进行归纳类比,把它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系列之中。便是在这里,本南丹蒂与萨满之间的相似之处,给我提供了不容反驳的证据。在两种情形下,这些个体的身体或心理特征——通常与其出身有关——令他们得以成为专业的出神者。在两种情形下,出神都伴随着灵魂出窍,而且通常是以某种动物的形式。在两种情形下,萨满或本南丹蒂的灵魂都会有涉险体验,而社群的身体健康或物质丰裕有赖于这些体验。
我在《夜间史》的前言中解释过,我并未探讨本南丹蒂与萨满之间在我看来“不容置疑”的联系,以免跌落到纯粹类型比较的层面。我宣称,这样做是在效法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榜样,他在《国王神迹》(Rois thaumaturges)中,曾对比了两种比较研究:一种是严格史学意义上的比较,比较历史上发生过接触的各个社会中的现象;另一种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比较,比较那些并不存在历史文献纽带的社会中的现象。布洛赫在1924年的文章中,引用了弗雷泽(Frazer)作为第二种比较的范例。但在几乎半个世纪后,这个问题依然无法以同样的办法予以解决。我们不得不着手进行的这种非历史性的比较(comparazione astorica),在我看来,是与列维—斯特劳斯一个路数的。在我撰写《夜间的战斗》时,有时候,我会试想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我的文献证据:一种是历史性的,另一种则是形式—结构性的。我的感觉是,选择第一种(正如我后来的确这么做的),我将无法充分论述那些看起来于史无凭的元素:首当其冲的,便是本南丹蒂与萨满之间的类似之处。
这种“历史或结构”的两难选择,在70年代中期再度浮现,当时,我决定去面对那些在《夜间的战斗》中悬而未决的、涉及范围大过弗留利地区的问题。与此同时,我的态度也在两个显然相反的方向上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我不再想从自己的研究中排除掉那些非历史性的关联。另一方面,我不再那么确定,本南丹蒂与萨满之间的关联只是单纯的类型关联。第一条路径让我跳出了历史书写;第二条路径则将我又带回了历史书写,只不过借助了一个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能会判断为不可能的问题。
我最终写出来的这本书——《夜间史》——正是这些相互对立的压力所产生的结果。这本书开篇的第一部分确然无疑是历史性的,它以一个阴谋论的出现为中心,而这个阴谋论正是宗教法庭对巫师夜间集会刻板印象的基石。其后的第二部分,则按照纯粹的形态学标准来组织编排,对一系列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有文献记录的萨满教类型出神崇拜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语境中,弗留利的本南丹蒂们再度现身,但他们只不过是万木丛林中的几株而已,而林中之树还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克雷斯尼基(kresniki)、高加索地区的布尔库扎塔(burkudzäutä)、匈牙利的塔尔托什(táltos)和拉普兰的诺阿伊迪(noajdi)。其中包括的匈牙利和拉普兰那部分内容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地区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居住在那里的人,其祖先来自(或可能来自)中亚地区。在匈牙利塔尔托什和拉普兰诺阿伊迪的例子中,与萨满的相似性尤为紧密。我们可以视其为一座桥梁,连接了中亚与弗留利、巴尔干半岛或高加索奥塞梯这些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区。如何解释这种地理分布?这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一章提出了一个历史解释,认为萨满教信仰与实践很可能是借助锡西厄人而从亚洲散布到了欧洲。锡西厄人所说语言是伊朗语族中的一个分支(因此也就从属于印欧语系),他们很可能来自中亚,在公元前数世纪时定居在黑海以北地区,并先后与希腊人和凯尔特人发生了接触。但是,题为“欧亚猜想”的这一章,在结尾处却强调了这些传播理论的局限: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文化传播可以用外部关联来解释,但只有内部关联,才能够解释这种文化传播如何得以长期持续。这一反对意见,将“历史与结构”的两难选择再度引至前台。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看来,这种从中取舍的不可能,与我内心深处以及周围意识形态动机的逐渐减弱有关。过去,在这些意识形态动机的推动下,我曾带着偏见得出了某个历史性的解释。我经常在胡思乱想中把自己比作布里丹之驴,纠结于两种同样站得住脚的文献阐释之间,竟把自己活活饿死(放弃把自己的书写完)。
这种两难选择,近来以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眼前。它是一种可能性:在我关于巫师夜间集会的书中,阿德里亚诺·索弗里(Adriano Sofri)发现了一个句子,提到打算以实验方式展示人性的存在,而他将这与我母亲所谓的“个人自然法(personale giusnaturalismo)”联系起来,并建议我考虑这样的一种可能。我问自己,或许,那个与此相对的、被我25年前作为起点的研究猜想,可以追溯至我父亲的历史决定论?我并不打算排除这种可能,即便这种一开始为我的研究指出方向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克罗齐的历史决定论(我在父亲的藏书中读到过他的作品,我父亲曾是他的紧密追随者),而是一种更激进的、因此被克罗齐否认与己有关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是由埃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在《魔法世界》(Il mondo magico)一书中提出来的。这个我此前绝对未曾意识到的心理维度的存在,很可能从两方面影响了我的研究。首先,它让我在面对这个长久与之缠斗的两难选择时手足无措(正如一个小孩在被问到是更喜欢妈妈还是更喜欢爸爸时会变得手足无措);其次,它也推动我去寻求一个不仅能与文献资料提出的要求相容、也与我的心理需求相符的解决方案。
让我来澄清一点:我并不认为,我给出的这些关于自身研究的具体答案,都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但我想,这些答案要想被接受采纳的话,必须不能与无意识中的心理否决对着干,而这种心理否决,完全可以将它们视作荒谬绝伦或无凭无据而加以拒绝。如果这种否决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确实存在(肯定并不仅仅存在于我的个例之中),我便能够回过头来理解,当初面对两难选择绕道而行的那个决定,为什么会被接受采纳。这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二章,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它试图将历史的视角与结构或形态学的视角结合起来,对汇聚于巫师夜间集会这个刻板印象中的信仰复合体的一个单一元素进行分析,这个元素,便是魔鬼的软弱无力。我没有办法对这非常复杂的论证过程进行简单概述,但这个论证过程的确让我找到了一根共同的线索,将俄狄浦斯和灰姑娘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相差悬殊的人物连在了一起。但是,即便是对《夜间史》如此浮光掠影的简单介绍,也足以表明,历史和形态学在书中并非对立并置(比如在那个后来被我放弃了的《夜间的战斗》双重版计划中),而是相互交织:两个声音此起彼伏,探讨对话,最终寻求某种和谐一致。这个选择,映射出了在我撰写《夜间史》的这15年中一直在我心中进行着的探讨对话。

(本文摘自卡洛·金茨堡著《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鲁伊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上一篇:股票定义及交割日介绍
下一篇:国泰君安网页入口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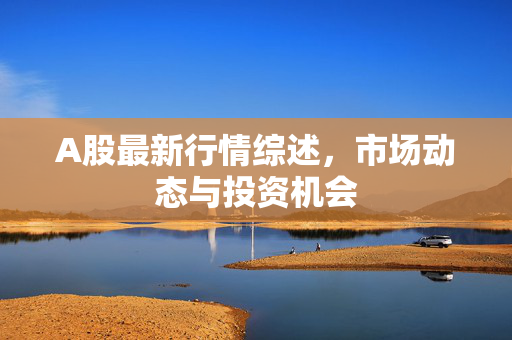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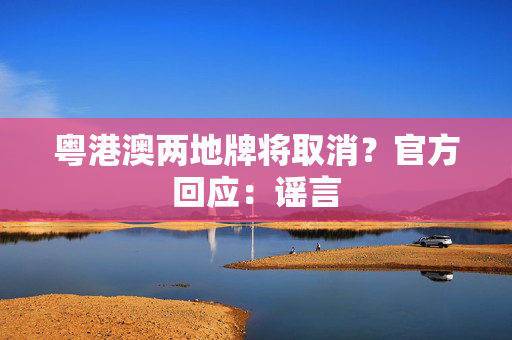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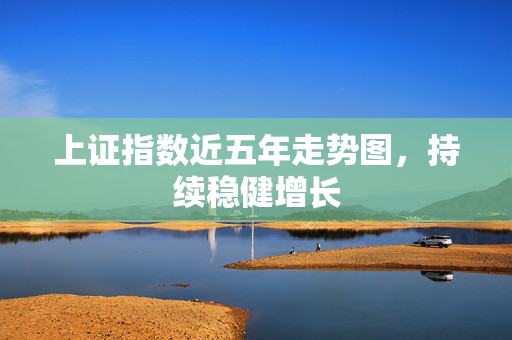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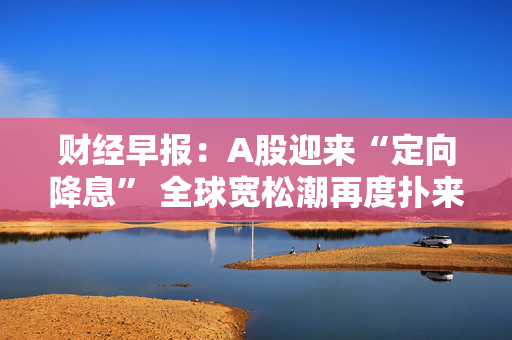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