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一条文学传统的暗线
- 外汇分析
- 2025-04-17 07:12:04
- 13
诗人、学者戴潍娜在新书《学坏》中,她选取鲍勃·迪伦、普希金、乔伊斯、波伏瓦、玛丽莲·弗伦奇、伊藤诗织、林奕含、赫胥黎、泰戈尔九位作家,从一位诗人的视野出发,理解属于他们身上“反派又迷人”的部分,打捞出一条文学传统的暗线。
日前,戴潍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在她看来,诗人的身体里有“异血”,得以在相似的风光中看到新鲜的风景,通过诗和美,将我们从眼前单一的生活里解放出来。

戴潍娜
澎湃新闻:《学坏》选取了九位不同时代的作家,你最看重的是他们身上的哪些特质?
戴潍娜:这些剑走偏锋的人物,他们身上异端和禁忌的部分如此迷人,我因而对他们拥有了一份私人情感。所谓的“正教”跟“异端”都在不断地彼此转换,今天的异端可能成为明天的正教。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他做了一系列的“天才研究”和“犯罪研究”,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正常”,往往是被过度修饰后的一种堕落。“正常”里,有着最大的奴性和惯性;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却说不定潜伏着某种天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认知革命,都是从这些“不正常”里来的。
我从博士四年,到进入研究所八年后的今天,研究兴趣都集中在持续打捞一条传统的“暗线”。对于“地下”“暗物质”“负空间”里的文学传统,有着一份格外的迷恋和执念。希望能在人类正经的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之外,去发掘一条被阉割的暗线。而这条暗线里,恰恰储存着人类思想撒旦式的爆发力——它始终在检阅历史和认知的红线。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天道变了,人道也要跟着变。那如何去适应一个新的天道?今天世界正在渐渐变成一个模子。尽管西方国家比我们更提倡多元,但这种多元更多是在物质上、情绪上、想法上,深层的思维模式上仍然是单一的。我觉得,在这条传统的暗线里,这些异端里,恰恰是存在着认知和思维方式上的极致多元。正是异端,保持了这个世界的弹性。它让每个人不沦为同一色彩的人,去反抗人人都是工具人的未来。

《学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闻:之前你说“我在这部书里面在寻求一个‘诱惑’和‘觉醒’的双螺旋结构——人类所有反思和争论其实都来自诱惑……”结合书名的《学坏》,怎么去理解这种诱惑(诱惑者)与觉醒(受害者)的双螺旋结构?
戴潍娜:《学坏》里,“坏”是一种冒犯的艺术,反叛的策略,僭越的精神,失格的传统。“学坏”这俩字,假使用不同的重音和停连去读,会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读法和意义。
伟大的引诱者,和令整个世界不安的觉醒者,构成了文学世界的阴阳两极。我在这本书里特别突出了一类女性主义觉醒式的写作,把它归纳为一种“幸存者文学”。在过去,受害者被永恒压抑在施暴者的胯下,永远沉默。我们过去对于犯罪叙述的逻辑都是错误的。大家都很熟悉洛丽塔,试想如果小洛丽塔自己拿起笔来写一部《洛丽塔》,那必定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类似林奕含这样的沉默受害者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被更多人听到,我觉得是有历史性意义的,甚至是性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番新的革命。从自白派传统开始,女性作家就在践行一种“不体面写作运动”,她们无疑拓展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
曾经的书面化世界里,我们所有人,不管男女,多在用男人的感知去体历世界。你会发现历史上都是男人在替代女人讲话。古诗里的闺怨诗,大多不是姑娘写的,而是爷们儿模仿姑娘的杰作。像杜甫当年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他是用妻子的口吻去描摹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他代替妻子在慨叹。整个人类历史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除了像卓文君、李清照这样出身不凡的名门才女和有艳情可以八卦的青楼名妓,普通人家的女人写的闺怨诗,大多出不了闺阁。《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女性4000多人,其中清代有3660人。也就是说清朝以前的女性创作者留下来的才340人,其中略有名气,大众知晓的,几双手就能数得清。
唯有女人自己开口,幸存者自己跳出来讲话,这个世界的感知维度才会因为她们的发声而翻倍。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以一种建构性女性主义触角,重新编织一系列作家作品,切割历史又逃离历史,致敬女性又审判女性。将“性别”媒介化、装置化为文学、艺术和跨文化的秘道,进而重构“性感”的历史时间。

《历代妇女著作考》,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闻:这本书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最终篇的泰戈尔从年代上甚至早于书里的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将泰戈尔放在最后,这也和双螺旋结构有关吗?

泰戈尔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戴潍娜:爱读禁书,爱写诡书之人,难免最后陷入一种困境:思想上重重突围,生活上无路可走。你绝望地发现,自己的头脑日新月异,但生活依旧陈旧不堪。这样的撕裂下,一个人要么发疯,要么犯傻,否则无法自洽。请泰戈尔放在压轴,是因为他提供了一条人间的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这位诗人坚决地站在中间道路上,坚持着两边不讨好,左右不逢源的中庸之道。他熨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文字的容器空了又空,永久地注入时代新声。
语言系统将焕然一新
澎湃新闻:你说“诗人是一种根本性的身份”,身为诗人的经验和视角对于阅读和书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戴潍娜: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把一个人变成一个诗人,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把一个诗人跟一个常人,一个庸人区分开来。是阅读?知识?情怀?
真正成就一个诗人的,恰恰比这些简单多了。一个诗人之所以是一个诗人,只因为Ta身体里的血。正是这异血,让Ta在相似的风光中看到新鲜的风景,在同样的经历中获得别样的感受,在古老的天地间拥有崭新的世界。一个诗人总要一百倍的敏感,一千倍的强烈,他们因而趋向疯狂。陌生化的感受会转化为陌生化的思维和语言。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诗人、学者、翻译这些多重身份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戴潍娜:不求相互滋养,只求不相互伤害。
澎湃新闻:书的中部探讨了各种女性文学。你说要创造一套女性普世价值、一种女性政治,首先需要一套适配的语言。这将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怎样形成,或者说它已经在形成中了吗?
戴潍娜:语言会自己生成、生长。没有人能设计出一套女性主义的普世语言,但如果每个人努力擦除自己语言中的男权烙印,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将焕然一新。
很多作家、诗人都在悄悄实践这种语言上的起义。比如一些韩国小说家尝试在她们的文本中改变一些词性。在韩国,过去如果你要讲一个女性作家,你一定要加上“女”,才知道这是一个女性,否则“作家”这个词天然就代表男性;再比如,韩语里对于男性称呼有很多敬语,但是对女性就没有那么多,于是新一代小说家试图在写作中改变这些陈词滥调。我有段时间跟一个俄罗斯诗人合作校译一首充满冒犯的女性主义长诗。那首诗歌特别难翻译。因为诗人把俄语里一些性化的词全部改掉了——她创造了很多字典里没有的新字,充当了新世纪的女仓颉。

鲍勃·迪伦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在对于鲍勃·迪伦和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解读里,你都谈论到了女性对他们创作的影响和滋养,这个角度往往是少见或者被忽视的,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去探讨男性作家身上的某些“女性气质”能带来什么启发吗?

詹姆斯·乔伊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戴潍娜:传统叙述中,很多时候男性被默认为“创造者”,女性则充当“缪斯”角色——别看缪斯有着“女神”的名号,实际是创作中提供素材和打下手的“女仆”。从乔伊斯对诺拉的狂热投射,到毕加索对情人们的艺术榨取,我想,去探讨这些男作家身上的“女性气质挪用”。
另一方面来说,好作家都是“雌雄同体”的。像伊利格瑞这样的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女性的呐喊不应该以男性作为比照而存在,更多的是在发掘女性生命本质的内在体验。伍尔芙也有这方面的自觉,她的《奥兰多》讲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男性贵族奥兰多经历一系列的爱情失望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变成女性,重新以女性的身份去体会这个世界,才意识到原来作为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麻烦。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除了权力的抗争,必然也包含一份感知上的性别觉醒——让男性与女性都能够跨越自己的身体,去体会到沉默的另一半世界。
澎湃新闻:波伏瓦在《第二性》里说到了阅读,认为大多数的女性阅读和写作仍然像钩织毛线一样,是打发时间,女性仍然处于内在性里,只有反抗社会不公的抗议文学才能产生真诚有力的作品。在《学坏》中的几位女性作家似乎都符合抗议文学的标准。你会怎么看波伏瓦的这个观点?

波伏瓦 三联生活周刊 图
戴潍娜:以后不会再存在像钩织毛线一样打发时间的阅读和写作了,人们都去刷视频了。能存留下来的阅读和写作,一定是有内在强度的。它们是给那些渴望有强度的灵魂准备的。
这种强度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抗议”(其中不乏优美的温柔的抗议)。《学坏》中涉及的女子文章,都是不绣鸳鸯只屠龙。对于那些“无能为力”“习以为常”“从来如此”“理所当然”的显性或隐性压迫,她们亮出自己的态度和刀锋,不让生活滑入庸常和惯性。
到最后,所有的诗与美,都是为了解放我们,让眼前的生活不是唯一。
澎湃新闻:在书的附录里你谈到了人的匮乏,在如今deepseek等AI开始越来越多被运用到“创作”中时,你是否认为我们变得更加匮乏了?
戴潍娜:当“尺度”巨大到一定规模时,有些问题就不再存在了——比如七尺的人会得癌症,但几十米长的鲸鱼体内永远不会长肿瘤。这种障碍对鲸鱼而言,天然不存在。当AI开始无限渗透进创作中,原本人文主义框架下的一系列关于人类本体的问题,都可能自然湮灭。
如今,我们人类所有的文明创造,都在迅速沦为计算机原料,我想那将是马克思“作为原料的人”最可怕的实现。
上一篇:各板块代码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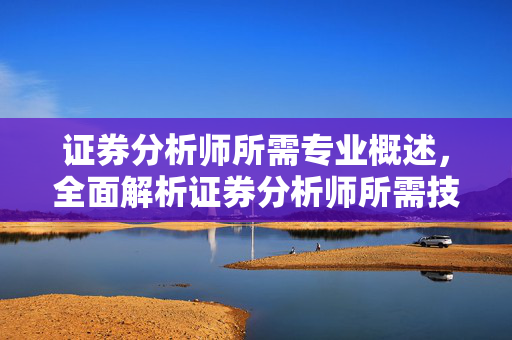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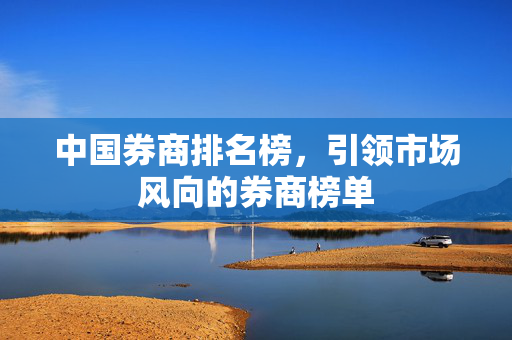






有话要说...